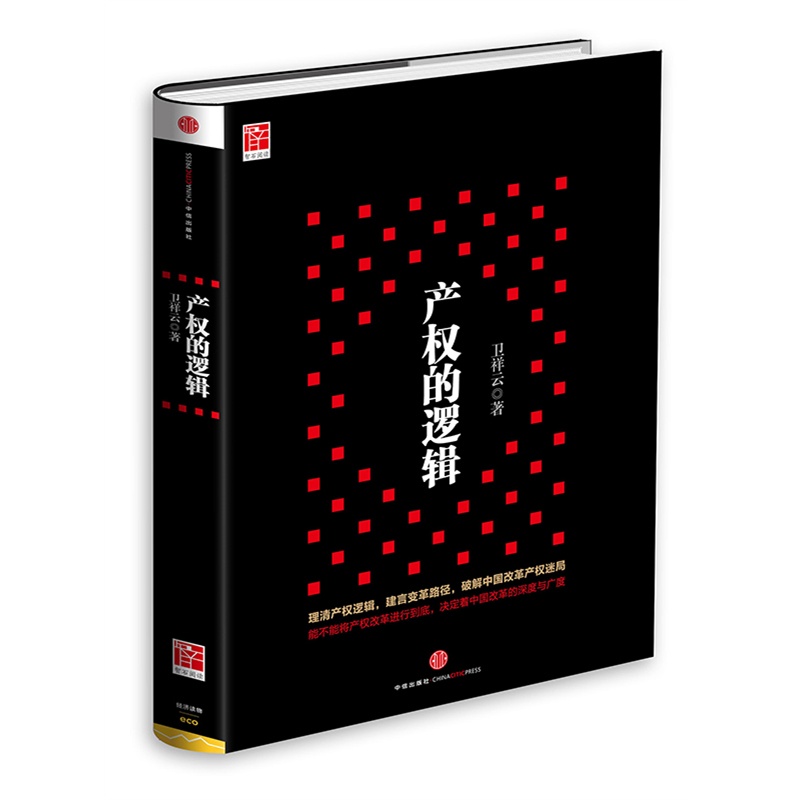食品安全监管升级能否打造安全餐桌
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每每“出事”,总是会沸沸扬扬地闹上一段日子,直到某一个部门站出来——有时是质检部门,有时是卫生部门,此外工商、农业部门也多少有过表态——只是谁也不确定,哪个部门负全责。
而今,人们的目光更集中地看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食药总局”)。
这个今年3月新组建的部门,注定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成长,其一举一动都让人好奇:散落在各个部门的监管职能“融为一体”,能否实现无缝监管?食品安全推行“大部制”,加上机构升格,到底带来哪些变化?最重要的是,新组建的“大食局”担负哪些监管责任,能否从此带来中国食品安全的“大时局”?
评判一个刚组建的部门还有些早,但新情况已经在发生。
8月2日,恒天然集团向新西兰政府上报其生产的浓缩乳清蛋白粉被检测出肉毒杆菌,就在8月4日中午,食药总局已经公布了当天早上约谈3家企业相关负责人的情况,“若企业对问题食品召回不及时、召回不报告,食药总局将采取严厉的监管惩处措施,直至该企业产品停止在华生产销售。”
透过约谈的“迅速”、“严厉”,多少能看见“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意味——这正是过去十多年间,人们所期待的。
“本轮改革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将分段监管变为分事项监管。”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长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在他看来,国内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推动着相关制度的演进。
上世纪80年代起,由卫生部门来管理食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仅监管食品卫生已无法切合现状。后来农业部门、发改委、商务部门从行业管理的角度监管,质检、工商、卫生等部门从执法角度监管。2004年,国务院以发文的形式,把“分段监管”写了进去。
多个部门如何监管同一领域?在研究者看来,这种监管或可称为“发证式监管”。发证的权力可以带来寻租的空间,让一些部门把持着食品安全监管职责,不愿放手。华南一位学者调研发现,一个县级市的蛋糕协会不得不通过投诉信的方式,向市政府反映两个部门争夺抽检费。
分段、多头监管的模式弊病,在2003年阜阳奶粉事件后已为人所察。当时国务院赴阜阳专项调查组曾指出,这一事件暴露了当地执法部门“执法不敏感,相互之间配合有差距”。这在之后被归纳为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七八个部门管不住一头猪”、“十几个大盖帽管不住一篮菜”。
改革势在必行。2010年,由三位副总理牵头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下设国务院食安办。胡颖廉去浙江省调研,看到浙江省市县三级都做实了食安办,“现在看来,当时的高配置,也是给现在的改革埋下伏笔”。
2013年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公布,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食品药品监管局、质检总局、工商总局4个部门的相关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职责聚拢在一起,组建为正部级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原商务部的生猪屠宰监管职能交给农业部。
这意味着,除农产品之外的食品安全监管,基本都由食药总局掌控。此外仍有一些职能在其他部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食品标准的制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食品包装材料、容器、食品生产经营工具等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的监督管理等。
食药总局综合司负责人孙梅君表示,这次改革对过去分段、分头监管的体制弊端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任何一种事物都不是孤立的”。
“本轮机构改革还是有限整合,不搞大部门。所以还没有把农业部和食药总局并在一起。”胡颖廉说,这相对以前的格局已经有了很大改进,确保有一个部门把最重要的精力放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出了事儿,将会更清晰地找到责任人,这只是第一步。未来这个部门还可以在风险监测、预判和预防制度上努力,尽量做到事前监管,而不是被动地‘收拾摊子’。”
改革之后,厘清监管者的责任至关重要。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拿出“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说法,从文字上来讲四平八稳,无可厚非,但决不能因此淡化了监管者的责任。“这就像一个考场里有学生作弊,监考老师是要负责的。”
然而,“监考老师”的身份总有点暧昧。“政府一方面要促进行业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挑毛病,利益相互矛盾,导致大量出现监管者行政不作为的问题。”杨小军说,当一些地方整个村都在造地沟油,这就不完全是村民的问题,而是监管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杨小军说,无论是瘦肉精还是地沟油,都应该正确地评估,监管者干了些什么,如果是“老师”和“学生”一块儿作弊,就要实事求是地针对这种情况,作出相应的对策,一味强调“企业是第一责任人”这种不够全面的判断,会导致对策偏差。
“食品安全领域的监管责任,应设立考核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来倒逼。”杨小军说,目前中央层面对此的处理是到位的,以后地方上能不能做到位,要解决启动责任追究的程序问题:谁来启动,多大责任,如何追究。“现在这一程序还是模糊的,靠领导批示与否,看媒体的报道和社会的反应。未来应该压缩人治的成分,以法治的思路进行下去。”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解志勇指出,《食品安全法》责任条款规定过于笼统,监管部门之间的责任区分或责任领域必须清晰。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则表示,食品安全的法律责任应该是行政、民事、刑事法律责任相结合。比如美国有非常高昂的惩罚性赔偿,这种惩罚性赔偿和典型案例一公布,才能在社会上形成威慑力。
“《食品安全法》中应该有一个专章来规定关于食品安全的问责制。”杨小军说,“实践中更多的是执法问题,只有管住各级政府官员,才能管住这个事。”
怎么让“哨兵”都到岗
按照国务院要求,食品药品监管要在6月底实现省级机构组建,9月底地市级机构组建完毕,年底县一级机构组建完毕。用杨小军的话说,这意味着“把责任分到人头,进行网格化监管”。
然而,监管网格上的“哨兵”们到岗了吗?这是目前业内人士最关心的现实问题。
“基层承载着13亿人口,是食品的主要生产、流通和消费场所,因此风险聚集和多发。”胡颖廉说,近来发生的“病死猪”、“毒生姜”、“假羊肉”等事件,问题源头都在基层。在现行体制下,大量监管人力和设备集中在省、市层面,质监、食药和工商等监管机构只设置到县一级,全国80%以上的县乡镇村没有专职人员和机构负责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和百姓饮食用药知识普及。
此外,监管队伍的技术水平和执法能力还远远落后,其规模与行政管理人员出现“倒挂”现象。胡颖廉表示,2011年全国食药监系统拥有行政管理人员5.3万人,但技术队伍仅有3万余人,上述人员中拥有GMP、GSP等专业检查员资质的更不足1.5万。执法过程中普遍存在“以罚代刑、有案不移、有案不立”等现象,即用行政处罚替代刑事责任,很难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事实上降低了监管对象的违法成本。”
胡颖廉测算过,如果把全国的乡镇街道都布点,保守估计需要增加15.5万监管人员,如此庞大的监管队伍,不可能靠新招聘公务员解决,必须采取灵活的办法。 “眼下,各地都面临同样的难题:钱的问题、人的问题、设备的问题。”
比如,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更愿意留在工商系统,不愿“折腾”。另一些部门则不愿意把人手划转过来。很多县级质监和工商部门通常只设1名股级干部专司食品安全工作,但实践中往往是混岗工作,在划转的时候常有单位不愿放人,“就让负责的那个人去做吧”。此外,各地都存在专业检测设备欠缺的问题,质监部门到底要划转多少设备给食药部门,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各地情况也不一样。
今年6月,有关领导在谈到转岗问题时特别指出,要按一个部门在食品安全上投入的工作量来划转人手,比如原来这一职能占质监或工商三分之一的工作量,那就按编制划转三分之一的人员过来。
胡颖廉还建议,目前可根据工作量划转工商部门监管人员、地方配套事业编制人员和招聘协管人员三种渠道相结合,即“正规军+地方军+民兵”的组合模式调配人手。在检测设备的问题上,一些地方尝试成立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作为事业单位,各部门按需要去向第三方采购,“尽管各地的进程不一样,但还是有不少解决思路。”
“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者对其期望很高,但部门衔接怎么样,和地方现实怎么磨合,利益如何博弈,一切都有待观察。”杨小军表示,食品安全领域的问题,不能看作是某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或道德标准问题,而应假定全世界市场里,所有的生产者都是唯利是图的,必须由公权力进行监管,不让其无所顾忌地对待消费者。“要靠制度而不是靠人,去抑制恶的一面,发扬善的一面。”